 摘要:
从梁思成的一句话,揭开中国古代石碑的神秘面纱经历书写材料的两次革命,制作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为何仍能贯穿两千余年的历史?石刻的兴造、磨灭、重刻,本身便构成了古人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
从梁思成的一句话,揭开中国古代石碑的神秘面纱经历书写材料的两次革命,制作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为何仍能贯穿两千余年的历史?石刻的兴造、磨灭、重刻,本身便构成了古人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曾到山西、河北农村考察古建筑,他的文字透露出“石碑”在当地村民心中的地位。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凯旋门……气势磅礴、规模巨大的纪念性石刻,在世界所有文明中都很常见。虽然传统中国没有金字塔这样的纪念性建筑,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却不乏纪念碑。墓志铭、善政碑、神祇碑……这些石刻历经千年存留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景观。
提图斯凯旋门。位于意大利罗马,门楣上刻着的文字大致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天才韦斯帕芗·奥古斯都之子天才提图斯致敬。”
经过两次书写材料的革命,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为何能延续两千多年?巫鸿认为,石头的坚硬、古朴,尤其是坚固耐用的特性,使它与“永恒”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象征着死亡、永生和升华。而它难以雕刻的特性,使它受到世人的珍视。古人曾说:
“又恐后人不知,便写于竹帛之上,以传后人;又恐其腐朽失传,后人无从记,便刻于盘碗之上,镌刻于金石之上,以存之。”
西王母坐昆仑图。嘉祥嵩山小师庙西壁石刻,东汉末年,2世纪下半叶。1978年出土。
因此,石刻成为担负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碑,石刻的创作、抹去、重雕本身构成了古人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隐秘而精彩的“无声”历史。
巨幅而沉默的石刻,如何折射出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竞争和社会心理?安史之乱后,唐廷与士人如何对待乱世中投奔安史政权的“叛徒”?中央与地方的授德碑又蕴含着怎样的政治互动与微妙心态?邱鲁明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一书通过石刻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探究了中晚唐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演变,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长安中央政府与河北诸侯国之间的种种互动,以及诸侯国内部复杂的格局。
1. 隐秘的角落:一个“叛徒”的人生史
文天祥在《义歌》中写道:“我是张绥阳之牙,颜长山之舌。”这里的张绥阳、颜长山,指的是唐朝的张巡、颜杲卿。安史之乱时,张巡誓杀敌,咬牙切齿。颜杲卿城破被俘后,大骂安禄山,被人钩断舌头。文天祥以张、颜二人为忠义典范,但其实,我们仔细考察安史之乱时唐朝官员的表现,就会发现,像张、颜这样的忠勇官员,只是少数。
还有更大的一群人,是隐藏在史料角落里的特殊群体。他们有的是在安史之乱前后投降安史之乱的唐廷重臣,有的则是在安史之乱前夕投降唐廷的安史之乱将领,是颠覆两边的“叛徒”。王绩的墓志铭记载了这位“叛徒”在安史之乱中的跌宕起伏,也颠覆了我们此前对唐廷处理“叛徒”政策的理解。
王俊墓碑。
复辟之初新奥新澳门六开奖结果资料查询澳门一码一肖一特一中347期,唐廷对“奸臣”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政策,处以斩首、打死、勒令自杀等刑罚,而对安史之乱投降的将领则态度宽大,意图拉拢安史之乱残余势力。笔者认为,这种对待“奸臣”与“功臣”的不同举措,体现了唐廷以“忠”为标准,考核乱乱时期官员的政治表现,进而整顿官僚体制,重塑帝国正统。然而,战局的突变,让唐廷迟迟未能放开手脚,在史思明叛军夺回主动权后,唐廷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对“奸臣”和“功臣”都采取了绥靖政策。 由于这一政策的改变,王俊、萧华、邵硕等一直在多个阵营之间徘徊的官员在叛乱平息后得以继续在唐朝廷任职。
笔者还关注了当时唐人对“奸臣”的态度。与普遍印象相反的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普遍认为唐廷对“奸臣”的制裁过于严厉,对“奸臣”抱有同情。再加上正史正传对奸臣的虚伪行为轻描淡写,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当时文人对奸臣的态度。不仅如此,文人的私人书信中也流露出对奸臣的理解和同情。例如杜甫曾为王维作了一首慰问诗《赠王忠云为》,为其辩护。
如果把唐代两面派官员的虚伪行为放在宋代或明清时期,无疑会遭到文人墨客的鄙夷和唾弃——宋代的司马光、清代的赵翼都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和怀疑——但在唐代,他们却引起了文人墨客的普遍同情。笔者认为,这种落差源于“忠”的观念在中唐以后得到强化,并演变为一种无限的义务。在唐代,君臣之间的恩情关系还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即君主本人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抛弃一切官员匆匆离京的行为,其实率先抛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让臣民自己寻找出路。 另一方面,在唐人的观念中,臣民只需兢兢业业地履行本职工作,并没有为国捐躯的道德义务,这也体现出当时“忠”义义务的有限性。
《明皇入蜀图》。描绘的是唐玄宗西逃入蜀的情景。
这种对“奸臣”的同情与庇护在安史之乱后一直笼罩在士大夫的心中,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士人的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宋代以后,“忠”逐渐从一个普遍概念上升为规范士大夫行为的绝对道德戒律。
二、墓志铭背后的“变”与“不变”
有研究者认为,使用安史之乱年号的墓志铭中仍保留“皇朝”、“皇”字,而不使用“燕”或“大燕”,是当时人们在安史之乱中仍心系唐朝的矛盾心态所致。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商榷。在用唐名号和不用唐名号的墓志铭中,不乏与安史之乱有密切联系的人,而用“燕”名号的墓志铭中也有为国捐躯的唐朝忠臣。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这些中下层官员是否有能力和自觉进行“隐写”。 综合以上因素,这些墓志铭中唐名、年号的使用,仅仅沿袭了墓志铭书写的格式,并无“隐文”的深层含义。笔者强调,看待墓志铭文字,应以整体的眼光,慎重考虑书法习惯、作者的习惯从梁思成的一句话,揭开中国古代石碑的神秘面纱,甚至随意性等因素,不应单单对一个字做出过度的解读。
但唐、燕年号墓志铭的分布和数量,确实可以反映双方控制面积的增减。例如,随着唐军发起进攻,唐肃宗使用的至德年号开始出现在两京出土的墓志铭中;而安庆绪逃亡相州后,其使用的天成年号则全部出现在相州地区,反映出安庆绪领地不断缩小的窘境。
安史之乱地图。
丧葬是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对人们的丧葬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吕藏元夫妇张氏墓志铭记载了一场由政府主持的隆重葬礼。不过墓志铭记载夫妇二人于乾元二年(759年)葬于洛阳首阳山,但墓志铭其实是在山西芮城出土的。当时洛阳正处于史思明的统领之下。可见,由于洛阳失守,墓志铭的主体被匆匆埋葬在黄河渡口,早已做好的墓志铭则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隆重荣誉”。当时避难江淮的文人不辞辛苦地将逝去的亲人葬在两京,即便是暂时葬在异乡,至少还有墓志铭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然而,死于战争的普通百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的尸体只能由政府来收走,不然就会被遗弃在荒野,尸骨遍地。
不过,动乱之初,士大夫阶层还是有些“不变”的。士人保持着原有的人际网络,忠勇的唐朝和安、燕的新贵们也依然保持着私人关系。陷于伪政权的唐朝旧臣甚至还会为忠勇的唐朝安排葬礼、撰写墓志铭。唐、燕政权的士大夫群体联系紧密,原有的社会网络运转正常。
3. 纪念碑背后的政治游戏
作者关注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属国之间的互动与紧张关系。碑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不同于传统的金石学研究方法,作者关注碑石本身的物质形态,探究碑石的修筑、抹除、重刻过程今晚澳门三肖三码开一码,以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通过梳理分析初唐、中晚唐、唐末五代赏赐良政碑制度的演变,揭示看似稳定的赏赐程序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罗让碑的现状。
罗让碑为魏州刺史罗弘信于隆济元年(889年)为其父罗让被追授工部尚书而立。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文德年间魏州衙军叛乱,以及罗弘信扶持乐彦祯继位的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记载了罗氏家族及魏州镇内部的政治结构。作者一方面以碑文内容为依据,从传统政治史的视角分析唐末魏州的政治变迁,另一方面创新性地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探究河北藩镇立碑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 与以往认知不同的是,魏州巡抚在碑文中常常塑造忠诚的形象,忠诚、信实的理念在碑文中被反复书写和强调,反映出“忠”的思想依然是河北藩镇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引入“表达—实践”概念,探讨天朝魏博时期一系列政治格局的兴衰。具体而言,政治权力斗争过程属于“实践”层面,构建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属于“表达”层面。没有合法性,权力就无法长久维持。如果只有合法性而没有权力支撑,统治就会崩溃。因此,政治表达与实践缺一不可,相互依存。
田弘正投降唐廷,开启复辟之路。在长安,唐廷抓住这一契机,在长安为他修建田家庙。田家庙作为一道政治景观,象征着魏博“回归王政”;在河北,田弘正也以一系列政治表演展现新气象:从违反礼制的大宅院移居旧时的接见使馆处理事务、请裴度撰写壁刻、重建狄仁杰庙,这些都成为魏博回归王政的重要标志。最后,作者指出,随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紧张关系愈发明显,中晚唐的政治运作更多依赖于一种“政治默契”。例如,唐廷采取“遥领”的方式来处理藩镇藩王的自承问题。 事实上,这种政治修饰并没有改变藩属国自选的本质,至少在形式上维护了朝廷的尊严。朝廷与藩属国之间心照不宣,维持着君臣表面的合作。正是通过这种政治默契,政治“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和。
狄仁杰庙碑部分拓片。
4. 中晚唐历史的另一面
充分运用大量石刻是《长安河北间》的一大特色。传统研究往往将墓志铭、碑刻等材料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属物,多侧重文字内容,而忽视石刻的物质形态。笔者以出土墓志铭作为研究的核心材料,注重石刻本身在历史中的作用,结合文字材料,追溯每一块石刻的修建、传播、修改、移动、存废,探究石刻背后的政治博弈和社会心理,描绘出一段“无声”的中晚唐历史。
本研究突破了旧有的历史框架,揭示了中央与藩属国之间以及藩属国内部复杂多样的面貌。陈寅恪、唐长儒等学者认为,中晚唐已分裂为唐廷与河北藩属国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但作者却雄辩地指出,藩属国虽然独立,但节度使个人统治权的合法性需要中央政府的授予,德碑因而成为“中央与藩属国博弈的重要工具”。从强大藩属国向朝廷请求立碑与朝廷应碑的互动过程中,作者敏锐地察觉到河北藩属国对中央政府“既反抗又依附”的矛盾心态。 藩属割据局面绝不是静态的对峙,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央与藩属国始终处于复杂的动态博弈之中。在双方力量的兴衰中,藩属国对中央既有顺从,也有反叛。
本书还对社会心理做了细致的考察。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奸臣”施以严厉的惩罚,文人对“奸臣”的同情也十分普遍。作者进一步指出,唐代文人的这种心态,源于“忠”的观念有限。在对洛让碑的研究中,作者还探究了碑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从碑文对“忠”的强调,可以看出当时河朔三镇的社会文化心理——普通军民仍然具有朴素的忠义观念。与一般印象不同,“忠”作为文化基础,在朝廷与藩属国之间,以及藩属国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稳定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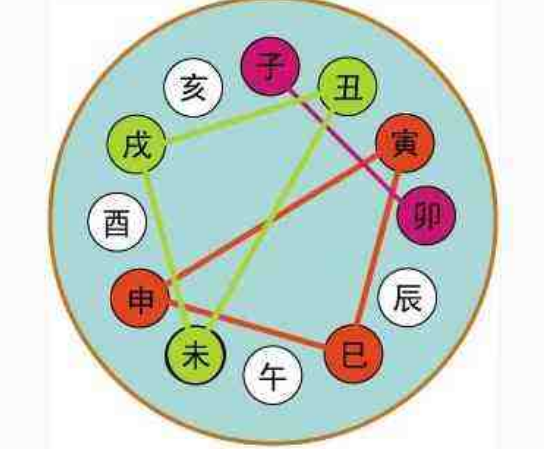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